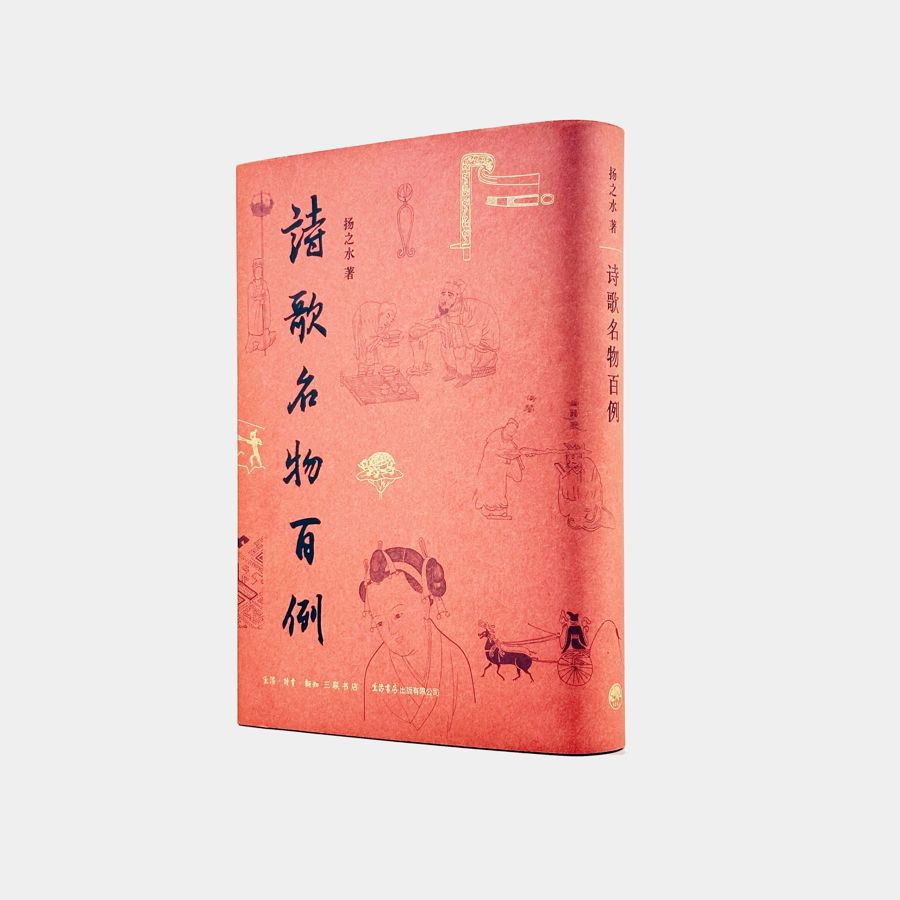一部《中国金银器》,对于中国金银器的研究堪称一次文化史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器中发掘关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进而考察它们的发展脉络。
面对沉默无言的出土文物,要做到一一引证有据、名实相符,此中艰难甘苦自知,按作者扬之水的话来说,只为一个最朴实的初衷:“它们就在那里,只等我叫出名字。”
扬先生的这本书中,构成叙事的器物图四千有余,绚烂如宋人的青绿山水长卷,它们都是她多年来在各地博物馆、特展中亲见目验的,后经仔细观摩思索、多方求证古籍文献后才下笔撰述。在由沈从文开启的“名物研究”中,扬之水通过融“物”入“文”入“史”的书写,赋予金银器以生命的气息。它所承载的文化史意义,正所谓“堪值等重之黄金”。
此为“名物志”系列访谈之五。

金银器兼具富与丽双重品质
上书房:“为金银立传”想来十分艰难,《中国金银器》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物,细数到清代的金银器物,用李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为《中国金银器》作序者)的话说,“需对古代文献与工艺技法了然于胸,又能用清隽的文字描述繁华奢靡,还要对市井生活的气息和颠沛流离的苦难有深切的同情,难为的事,扬之水自会去做”。这件事有多难呢?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金银器》是第一部中国古代金银器通史,囊括了器皿与首饰,着眼于造型与纹饰,究心于美术和工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
金银器兼具富与丽的双重品质。首先它是财富,其次它是一种艺术形态,然而通过销熔的办法又可使之反复改变样态以从时尚,因此人们并不存心使它传之久远。
相对于可入鉴藏的书画、金石、玉器、瓷器之雅,金银器可谓一俗到骨。它以它的俗,传播时代风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被人贪恋和追逐的角色。
与其他门类相比,金银器皿和金银首饰的制作工艺都算不得复杂,这里便格外显示出设计的重要性。在古典时代,这种不断开掘构图元素的创意,该会为追慕时尚的人们带来特别的欢愉。
上书房:您在《中国金银器》的“后叙”中写道:“一部书稿完成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一部尤其如此,因为它是我此生最费心力的一部书。”我脑海中浮现出您自2003年发表首篇研究金银器的文章《明代头面》以来,整整二十载无数次目验文物、埋首古籍的画面。您陆续出版过《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奢华之色》等研究金银器的书籍,《中国金银器》是否为集大成者?
扬之水:自师从孙机先生问学始,老师就告诫我: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去写文章,否则不要动笔。这一教诲我至今牢记。《中国金银器》不是之前几部书的“集大成”,而是各有侧重。比如作为附录分别收在《奢华之色》各卷的《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罚觥与劝盏》等专论,在《中国金银器》里只是用了文章的结论,并未展开讨论。可以说,既往我做过的诸多个案研究,是《中国金银器》的基础。
上书房:您对器物的诠释方式很独特,所采用的既不是考古学的专业术语,也不是登记物账所使用的周备的记述,这样的理解对吗?
扬之水:我所研究的金银器史,建立在对艺术语汇发生与演变的观察和分析之上。我力求呈现两类语言:一是“物”,用造型和纹饰表达自身的艺术语言;二是“文”,是人对物的命名,此中包括对物之本身和物所承载的意念之理解。
对这两类语言的解读,便是本书最基础、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我想借此回到历史现场,复活古典的记忆。因此审视研究对象之际,想到的首先是它的设计者和制作者,然后是它的使用者和欣赏者,所以书中宏观的判断式论述并不多,只是力求每一个判断都有足够的细节作为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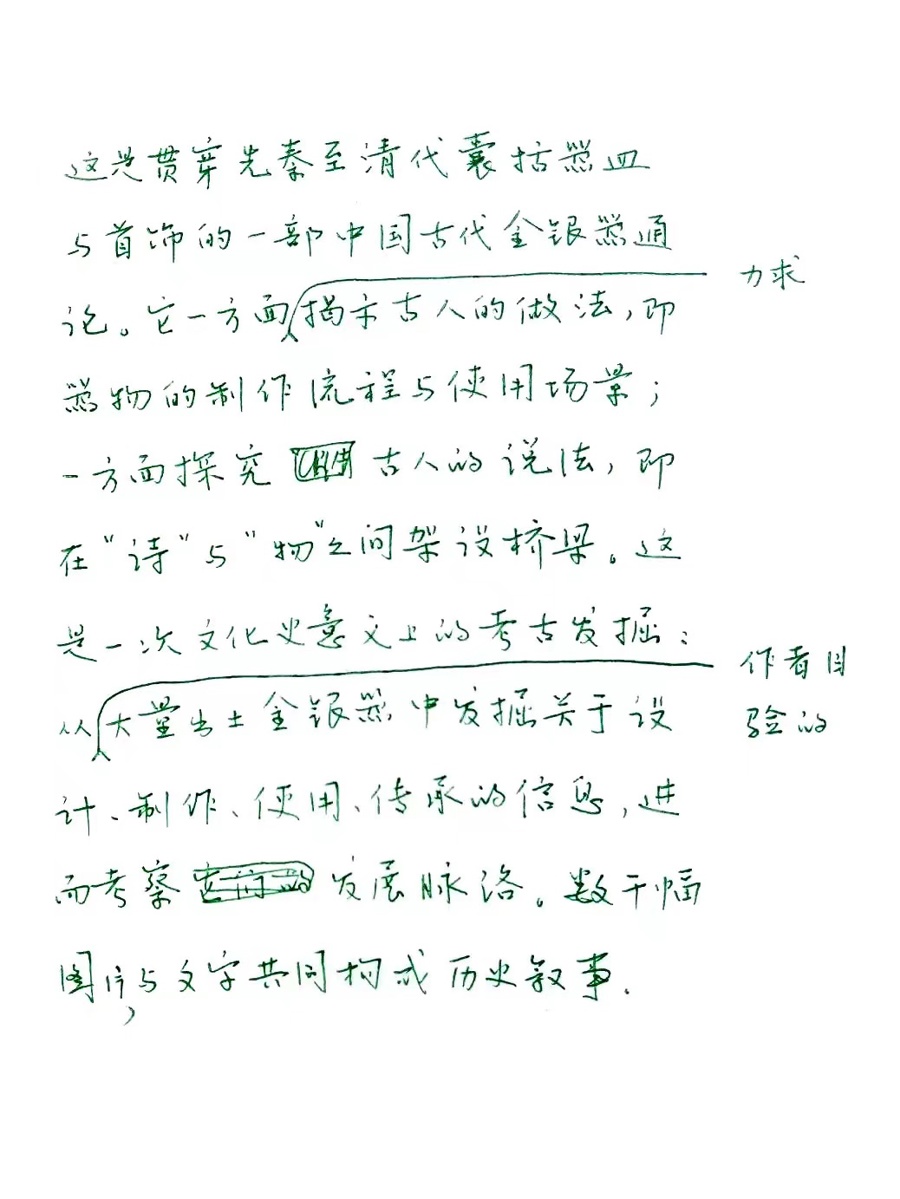
拼缀起曾经的生活图景
上书房:您从研究古诗词和古典文学中的“物”开始,聚焦研究过香具、字画、家具等等,研究哪个品类的物是最带劲的?您偏爱哪个朝代的“物”?
扬之水:对我来说,不存在研究某一品类的物“最带劲”,更不存在偏爱哪个朝代的“物”,因为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会去写文章,那么最有吸引力的自然就是所谓“不知名物”。引领我步入名物研究的是孙先生,当然也对我的研究最有影响。不过孙先生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名物,而是文物考古,文物考古是统领名物的。
上书房:给我们举一个您为古物定名的例子?
扬之水:先举一个关于香事研究的例子。我对香事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年,源自通读了《全宋诗》之后。主要想法我写在了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香识》的后记里:“中土香事原有着久远的传统,一是礼制中的祭祀之用,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焚香。魏晋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东传的香事之种种,不过是融入本土固有的习俗,而非创立新制。至于两宋香事的兴盛发达,却是与高坐具的成熟密切相关。其时士人的焚香,原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后世看的是风雅,而在当日,竟可以说风雅处处是平常。”“香料以及香料贸易的话题——食品调料与洁身除秽之香,也都包括在内,在域外并不寂寞,此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敏感的学者不会轻易放过的。相比之下我们这里就冷清得多,特色独具的香事连同香诗竟被遗忘了好久。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情景。只是相对于今日之热闹,仍不能不感慨当日撰写这些文字时的孤寂。”这一研究过程当然充满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
20世纪70年代末,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中兴复古”香饼一枚,我在2004年考证它为内家香。2015年1月我前往常州博物馆参观,特别向馆方提出请求看一看这枚香饼。原来它入藏后一直被称作香篆,馆里人说,因为搞不清质地,分类保管的时候就归在陶器了,又因为不知道此物的重要,没把它当回事,专家来这里定级文物的时候,都没把它拿出来。
那次我终于得见香饼真身。灰扑扑不辨质地的小小一枚,没有任何气味,模印的“中兴复古”四个字清清楚楚地隆起在表面。古物拿在手里分量极轻,历经八九百年风尘,一霎时竟入掌握。翻过来,我意外发现背面一左一右模印着两条蟠屈向上、身姿相对的龙,此物出自禁苑,这一点完全可以确定。几个月后,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香远益清——唐宋香具览粹”展览中,“中兴复古”香饼便第一次登场展示在公众面前了。就此成为名品。

上书房:金银器研究领域,也有这样难忘的经历吗?
扬之水:进入金银器研究的领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入口在什么地方?回想起来,当是看到《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的金银器卷中收录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中的一大批,其中对器物的定名多令人疑惑。比如被称作“发插”的20件元代饰品很可能是耳环;又所谓“金镂空双龙纹头饰”似为梳背儿,诸如此类。
机缘凑巧,我在2005年5月受邀前往湖南省博物馆举办关于明代金银首饰的讲座时,馆方提供库房观摩之便,看过临澧柏枝乡南宋银器窖藏之后,我向馆方提议合作研究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的课题,两位馆长当即表示支持。
由此,我开启了湖南十个县市的观摩窖藏金银器之旅,接着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与湖南省博物馆的合作课题。亲抚实物,证实了之前我在阅览图录时的推测,对制作工艺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在现场我有很详细的观摩记录,后来大部分成为《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书中的内容。书里我为首饰和器物的定名,如今已经被广泛采用。
其中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发现,参观株洲博物馆时,在展厅里看到出自攸县丫江桥元代金银器窖藏的一枝金簪。簪首绕图一周是枝叶纷披的朵朵菊花,花丛间一个山石座,座上一个金盆,略略俯身的一位女子,双手伸向金盆。展品说明作“金盆洗手图金簪”。“金盆洗手”是近世的一个俗语,有约定俗成的意思,用来为这枝金簪纹样命名,显然不合适。那么这一“金盆洗手”的场景究竟取自什么故事呢?归来后从文献和图像中寻找线索,找到宋元绘画中与金簪纹样一致的《浣月图》及明代的一幅《金盆捞月图》,而元散曲中正有与此情景对应的歌咏,题作《掬水月在手》。可知丫江桥金簪的取材是来自当日流传的同题绘画,即“掬水月在手”诗意图。
上书房:这样的考证过程,是否很有成就感?
扬之水:考证到了这一步,我仍觉得不够,似乎仍未找到源头。于是追源溯流一步步推进,终于勾画出了从诗歌到图画、由唐宋至明清,“无声”与“有声”互为影响、互为渗透的一个纹样传播史。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这一条线索使我们有可能拼缀起曾经有过的生活图景,并发掘出把诗意凝定为各种造型艺术的才智和匠心。”有评论说,“这篇论文是同时在文学研究和文物考证两方面取得成果的典范之作”,我很感念这样的认可。

看到它感到一阵狂喜
上书房:刚才您提到“线索”,在梳理线索、为器物定名的过程中,发现“关键线索”是否需要一些“运气”?
扬之水:我再讲一段没有披露过的故事。关键证据的发现,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最觉有趣的事。2012年3月我发表过一则《读物小札:人胜·剪綵花·春幡》,但总觉缺少关键物证。2014年初春,浙江省博物馆动议举办定州两塔文物展,我受邀随同考察,得以亲抚定州博物馆藏品,于是在观摩现场我发现了——应该说是认知,因为它久已在彼,只等待我去叫出它的名字——实物证据“宜春大吉”银春幡。
这件文物很不起眼,出土以来未见介绍,更不曾展出,原本是不在入选之列的。当时的心情,不妨用“狂喜”来形容。之后又发现出自宜兴北宋法藏寺塔基的镂花银饰片,饰片中间一方用于装饰吉语的牌记,其上打制“宜春耐夏”四个字,便可以立即断定它是春幡,南宋杨万里所咏“綵幡耐夏宜春字,宝胜连环曲水纹”,正是此类节令时物。
联系之前看到的不同时代的相关实物,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呈现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金钗斜戴宜春胜》,可以算是为时令节物春幡胜立传,它也就是我为自己订立的目标之一:名物考证应该包含着多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

上书房:听说您去参观文物展总能看出“故事”?
扬之水: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是追踪看展的结果。2013年,我参观了一场“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展”,金器展陈规模空前,近半数器物不曾发表,更不必说公开展览,真是远远超出预料。
满载收获的同时,也引起我的许多疑惑,如蕲春明荆藩王墓出土的一批金银首饰,在展览说明中出现这样的器物名称:“金球”“金镶宝石浮雕骑马交战头饰”“金镶宝石善财童子簪”……虽然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为器物命名,如上述三件器物为“金穿心盒”“三英战吕布银鎏金满冠”“金镶宝观音挑心”(挑心是明代簪的一种),但终究还是隔着展柜,细节不能完全掌握。特别是“金镶宝观音挑心”,从纹样特征来看应该是传统题材“鱼篮观音”,总觉得器物缺少一个关键道具:鱼篮。
2015年,我在蕲春博物馆看到一件文物“银篓里放金鱼”。此物取出来,我一眼认出它正是“金镶宝观音挑心”上面的构件——鱼篮。那么毫无疑问,这一枝挑心的纹样是鱼篮观音。然而博物馆的书记道:“鱼篮在,观音走了。”原来“金镶宝观音挑心”今藏湖北省博物馆。
我当然还要继续追寻文物。2016年5月,我又往湖北省博物馆,在库房零距离观摩此物,一方面可以肯定自己的推断,一方面看到了器物的更多细节,因此丰富了对它的认识。于是我为出土于明荆藩王墓的金银首饰一一定名,并促成它在浙江省博物馆以全新面貌展出,展品说明和同名图录中的器物名称及纹饰解读,大部分取用了我的意见。
如今,这些定名更是广为普及,而为公众采用。面对名物考证通常没有“知识版权”的近况,我想,考证成果被“公有化”,就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奖赏了。

用名物学建构新的叙事系统
上书房:这些年,随着“考古热”来袭,人们似乎越来越关注名物研究,其中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
扬之水:我觉得,当前人们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物”或曰“物质”,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名物研究,从事者还不多。
图像、物件、材质,普通的词汇如今都进入了思考的深层而被赋予理论色彩,由是生发出艺术史领域里层出不穷的伴随着新式表述的话题。
而我所理解以及关注和研究的名物之“物”,就是器用,并没有哲学意义或理论色彩。面对某物,最直接的问题必是:“叫什么名字?有何用途?”面对有叙事性的纹饰,最简单的问题必是:“有什么故事?”当然,问题很简单,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而乐趣也在这里。
上书房:名物研究如今有什么新的方式方法?
扬之水:所谓“新的方式方法”,其实依然是从传统方法中生长出来的。我把它总结为定名与相知。
关于“定名”,我以为,对“物”亦即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里面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
所谓“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时的用途与功能。我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重温古典。
文史研究要有闲的一面
上书房:科技加持之下,名物考证会变得比以往容易吗?
扬之水:近年来,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天的名物考证比以往增添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不过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的“金手指”也无从索检的,何况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也不是依凭“技术的加持”就可以解决,究竟还是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
上书房:这么说来,新时代的文史研究对学者的要求反而更高了?
扬之水:确实如此。我想到谢泳的《新时代的文史研究》一文,其中说道:“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原先记忆中存了的问题,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发生联想,再去检索,然后解决。”
谢先生说:“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语词,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所云令人深有同感,特别是“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趣味”,学术前辈是这样,自己也以亲身经历参与了同样的体验。
上书房:您近期在从事什么研究?
扬之水:我即将出版一本《诗歌名物百例》,出版方仍是生活书店。写作这本书的动因,源自老同事刘跃进执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时的叮嘱,即编纂一部诗歌名物词典,解决文学研究中的问题。
他的建议很叫人心动。然而时日迁延,我从在职到退休,从少壮到古稀,计划始终停留在计划阶段,总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所知太少,未知太多,前者是滴水,后者是海洋,因此这一计划此生已是无望完成。今以“百例”的面貌出现,是源自生活书店掌门人曾诚的提议。
古诗歌名物之所谓“物”,大致有两类:其一,天地自然之物;其二,设计与制作之物。《诗歌名物百例》乃着眼于后者。以诗为媒,我们会得古人投射于“物”的心思和情感;以“物”为媒,我们解得诗之所咏与所叹。在诗与“物”的契合处,我们得以与古人之诗笔通灵。可以说,这是自家做过与诗歌相关的名物考证之缩略版,即将长篇考证瘦身为几百字的词条而以图见“物”。